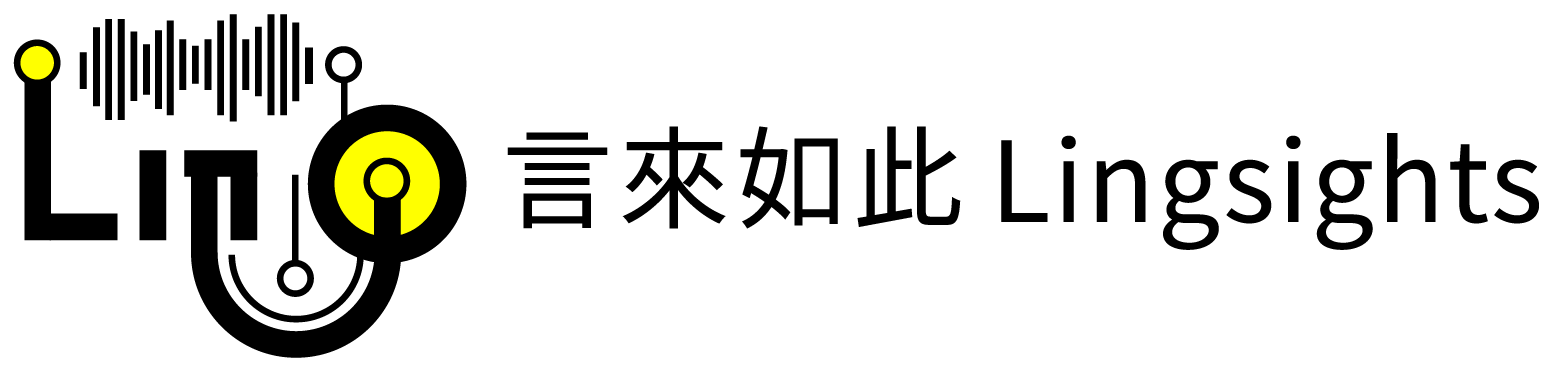平衡醫療觀點和社會語言學視角:可能嗎?
社會語言學視角側重於展現個體的神經多樣性和探討造成失能的社會障礙,但有時它未能捕捉到社會現實。有些失能者因為在生活中遇到的一連串的現實需求,而希望放棄他們的多樣性並融入主流社會結構中。即便醫學模型已經解決了其與語言正常化的負面聯繫,並正面的協助失能者擁有更多的自主權來實現他們的個人需求,社會上的條件和現實對失能者來說仍然具有挑戰性。

文:魏紹丞(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語言學碩士生)
看待失能和其相應的語言表現,有兩種相異的失能模型,一種從醫學或病理學的角度出發,而另一種從社會觀點切入。
在醫學模型中,人們就自身的語言表現被分為「正常」和「不正常」兩類,任何失能或不正常的語言行為都會被視為是需要改正或修復的缺陷。因此這種模型確立了「語言正常性」(language normalcy)為標準的觀點,因而病理化個別且獨特的語言使用方式。長期以來,語言使用被認為與個人能力和智力有關,因此不符合語言正常性的個體,其心智或大腦會被視為失能。透過治療過程,個別獨特的語言表現最終會消失,由外而內的趨向「正常」。
然而,醫學模型和病理化語言的觀點受到廣泛批評,因為此類模型體現了社會上的壓迫、健全主義、種族主義和不平等的政治權力。Henner 與 Robinson 兩位聾人學者從社會和失能的角度提出許多論點來反對病理化語言,他們主張沒有任何一種語言使用的方式是缺陷或失能,並呼籲社會上應該以更廣泛包容的態度來看待各式各樣的語言表現。以此為理念,他們提出了「打殘語言學」(crip linguistics)的觀點,透過社會語言學模型的詮釋,來理解和領會人類心智和語言使用的靈活性、創造力和多樣性。
社會模型以更開闊的方式來看待「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sity)和語言失能,認為真正阻礙語言使用獲得平等對待和社會正義的原因是社會結構問題而非個體上的缺陷。因此,解決語言失能的方式不是透過醫學治療來修正個體的語言使用,而是消除社會上對失能者的阻礙,增進社會上的包容性,和保留個人或特定群體的語言特徵來展現社會上身份或群體的多元性(如果失能者願意或希望這樣做的話)。
醫學和社會模型不僅對醫學處置的本質、社會正義的發展以及失能者的自我認同有重大影響,也顯現了在兩種模型間找到一個能使失能者從醫療護理和社會正義中受益的中間地帶的困境和可能性。本文中「失能」的定義是:擁有被視為需要改正或治療的特定狀態或表現。
並非正常化,而是緩解
如果要平衡病理和社會觀點,就必須最大幅度的降低醫療模型中語言正常性造成的影響。
醫學治療應該是提供了緩解身心痛苦的選擇,而非同質性的標準來做為正常化的工具,並強加在具有不同語言特徵的人身上。醫學模型或病理視角強調對失能者的正常化,而不是專注於他們實際的身心需求。
一些學者也以其他名稱來形容醫學模型,例如「個體模型」(individual model)或「人身悲劇模型」(person tragedy model)。這些名稱都突顯了醫學模型優先遵循語言正常性,並將失能和非失能的差異歸咎於的個體責任。譬如 Zaks 就認為應將醫學模型的名稱改為「正常化模型」。如此一來,醫學模型的實際內容就很明瞭,更改後的名稱更能夠直接表明正常化對失能者所造成的損害。
從名稱上有「醫療」二字上來看,會直觀的認為語言正常化僅由醫療專業人員或醫生進行評估或執行。但實際上,正常化是由懷有健全主義的非失能者在社會各層面,包括家庭、社群、教育和就業上強加於失能者的。因此,將名稱從醫學模型改為正常化模型,不僅讓醫療專業人員,更讓整個社會對消除有害的語言正常化負起責任。更正為正常化模型承認正常化的影響超出實際醫學上的治療,彰顯正常/不正常二分法的不公正,並讓醫療專業人員和社會對正常化造成的傷害和後果負責。
正如Johnston所指出的,語言正常化開啟了一種可能性,甚至導致了一個必然結果,即消除了澳洲大部分的聾人社群。正常性的概念已被套用在聾人群體,限制了聾人和手語社群的人口。Johnston 統整了三個導致澳洲聾人和手語社群衰退的因素 [6]:醫療系統的總體改善、產前基因檢測,以及對人工電子耳的偏好,而抑制了手語的使用。從這個例子來看,我們可以看到醫學模型中的正常化與社會上失能社群的生存之間的拉鋸,這毫無疑問的在未來三十到五十年內會對失能社群有很大的影響。
為了挽救情勢,Bauman 與 Murray 提出的可能性之一,就是把正常性最小化和去中心化,為進一步社會發展的可能性創造更多空間。因此,取得社會和醫學觀點之間的平衡的第一步是消除正常化,當我們釐清醫學模型的角色並目睹正常性所造成的危害時,才能看到醫學模型和社會觀點之間的聯繫。
排除一致性的修復和治療語言失能、感知和產出,可以正面的突顯醫學模型的本質實際上為了緩解失能者的身體或精神痛苦,以達到更高水準的生活品質。在這個觀點上,醫學模型不再是以一套標準化的程序來改正失能者,而是一個醫療援助來支持失能者達成他們自己設定的目標,融入社群,成為擁有多元身份的社會成員。因此,醫學模型和社會觀點之間的關聯可以建立起來。去正常化的醫學模型更有可能滿足個別失能者的各種需求,藉由醫療上的支持,失能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和目標在社會上自由發展。而且,去正常化更能夠停止病理化語言,因為每個人的語言使用都有其獨特性。
正如 Henner 和 Robinson 所指出的,人們各自使用語言的方式,反映了個別身體和心智是如何運作的。每個個體都是不同的,所以不必然、甚至不需要一個能夠概括正常語言使用的規範。並不是因為大多數人都擁有某些特徵,那些特徵就應該被認為是正常性的定義和標準。病理化語言有可能消失,當每個人停止將帶有偏見和主觀的正常性強加於不與我們共享特徵的人。語言正常化是持續傷害和污名化失能者的原因,因此應從醫學模型中根除。
醫學模型的本質不應該是正常化失能者和病理化語言,而是提供醫療協助以緩解那些阻礙失能者生活和行動的身心痛苦。在平衡醫學和社會觀點時,醫療協助可以被視為連結失能者和其實際需求之間的一種方式。因此,去正常化的醫學模型交還了身體自主權和為失能者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讓他們擁有選擇權來成為他們可以但不一定必須成為的人,且根據自身的意願生活並沒有對錯之分。
社會與現實
社會語言學視角側重於展現個體的神經多樣性和探討造成失能的社會障礙,但有時它未能捕捉到社會現實。有些失能者因為在生活中遇到的一連串的現實需求,而希望放棄他們的多樣性並融入主流社會結構中。即便醫學模型已經解決了其與語言正常化的負面聯繫,並正面的協助失能者擁有更多的自主權來實現他們的個人需求,社會上的條件和現實對失能者來說仍然具有挑戰性。
從「臨床語言學與社會正義」課堂上針對聾人是否要糾正口音的訪談稿討論中,聾人受訪者對是否糾正口音的立場存在不確定性。就社會現實和生計方面考慮似乎是更支持聾人糾正口音,儘管根據受訪者和社會語言學的觀點,完全沒有必要這樣做。顯然,失能者所擁有的語言特徵與社會現實所需求的特徵之間存在矛盾,而根深蒂固的社會結構,對失能者在保持其群體身份或融入主流社會方面構成了重大挑戰。
正如 St. Pierre 所點出的,失能與工業化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具有效率的理念深深根植於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中。因此,口吃者因為社會上對工作執行和交流效率的高要求,而無法被視為是具有足夠工作能力的人。如果一個人不能保持專業的交流速度,口吃就會被放大成為一種經濟層面上的累贅,因而造成口吃者被排除在社會和經濟交流之外。從聾人和口吃者的例子中可以明顯看出,某些語言表現與社會需求間存在不相容性,特別是與經濟相關的層面上,而這給失能者留下了很少的選擇空間。
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看,一種方法是提倡一個包容性的社會結構或工作環境,了解其實在對話交流中的責任不是單方面的,而是落在每個參與者上,當對話上遇到困難時,參與者有同等的責任。例如,口吃者的講話可能不連貫,而聽者也可能急於替口吃者完成句子,或錯誤地假設口吃者即將說的話。實際上,雙方的語言行為都阻礙交流的順暢程度,因此不應該只讓口吃者承擔責任,並因此被排除在經濟與社會交流之外。
另一種方法是訴諸去正常化的醫學模型,此模型為失能者提供醫療協助,以實現他們設定的目標。每個個體對其身體如何以及何時開始和停止醫療協助擁有充分的自主權,提供更靈活的方法來應對他們的現實需求,並為成為不同社群的參與者打開了可能性。如果個別聾人和口吃者願意或希望為了某些原因改變口音和講話節奏,那麼醫療協助可以幫助他們,但這不是為了正常化,而是為了實現個人目標和價值觀。
如果我們理解兩個模型分別扮演的角色,那麼平衡醫學和社會觀點是可能的。社會模型的角色是消除社會障礙,建立包容多樣性的社會。然而,有時候社會模型並不是那麼接近失能者的實際需求。因此,去中心化的醫學協助可以介入。這不僅僅是為了緩解失能者的身心痛苦,還提供實現其實際需求和確定目標的方法。社會語言學視角展示多樣性,醫學模型重視個人意願。
要平衡病理和社會觀點就需要最小化語言正常化的影響。醫學模型將失能歸因於個體責任,而不是強調解決失能者真正的身心需求。去除正常化之後,醫學模型更能將重點放在緩解痛苦和支持失能者實現其自我定義的目標、融入社群並自我認同。消除醫學模型中的語言正常化能夠使多元的語言使用不再被汙名化,並賦予失能者按照他們意願生活的權利。社會語言學視角突顯神經多樣性和導致失能的社會障礙,但有時未能解決失能者在現實中的實際需求。
通過理解各自對失能者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實現醫學和社會觀點之間的平衡。社會模型側重於消除障礙和創建包容多樣性的社會,而去污名化的醫學模型不僅緩解身心痛苦,還提供滿足實際需求和個人目標的方法。社會語言學視角強調多樣性為社會的最終目標,而醫學模型尊重實現個人意願的自主權。
參考文獻
Bauman, H. D., & Murray, J. (2009). Reframing: From hearing loss to deaf gain. Deaf Studies Digital Journal, 1(1), 1-10.
Bunbury, S. (2019). Unconscious bias and the medical model: How the social model may hold the key to transformative thinking about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crimination and the Law, 19(1), 26-47.
Easton, C., & Verdon, S. (2021). The influence of linguistic bias upon speech-language pathologists’ attitudes toward clinical scenarios involving nonstandard dialects of English. American Journal of Speech-Language Pathology, 30(5), 1973-1989.
Flores, N., & Rosa, J. (2015). Undoing appropriateness: Raciolinguistic ideologies and language diversity in education.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85(2), 149-171.
Henner, J., & Robinson, O. (2023). Unsettling languages, unruly bodyminds: A crip linguistics manifesto. Journal of Critical Study of Communication & Disability, 1(1), 7-37.
Hobson, H. M., Toseeb, U., & Gibson, J. L. (2024). Developmental language disorder and neurodiversity: Surfacing contradictions, tensions and unanswered ques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Johnston, T. (2006). W (h) ither the Deaf community? Population, genetics, and the future of Australian Sign Language. Sign Language Studies, 6(2), 137-173.
Nario‐Redmond, M. R., Kemerling, A. A., & Silverman, A. (2019). Hostile, benevolent, and ambivalent ableism: Contemporary manifestation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75(3), 726-756.
Oliver, M. (2013). The 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 Thirty years on. Disability & Society, 28(7), 1024-1026.
Pierre, J. S. (2013).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abled Speaker: Locating Stuttering in Disability Studies. In Literature, speech disorders, and disability (pp. 9-23). Routledge.
Riddell, S. (2018). Theorising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in a changing political climate. In Disability and society (pp. 83-106). Routledge.
Swain, J., & French, S. (2000). Towards an affirmation model of disability. Disability & Society, 15(4), 569-582.
Wendell, S. (2013). The rejected body: Feminist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disability. Routledge.
Zaks, Z. (2023). Changing the medical model of disability to the normalization model of disability: Clarifying the past to create a new future direction. Disability & Society, 1-28.
文章分類
作者介紹

陽明交通大學外國語文系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向以理工、醫學及管理見長,有鑒於科技的發展宜導以人文的關懷、博雅的精神,而資訊的流通則取決於語文的運用,因此於民國八十三年八月成立外國語文學系。
本系發展著重人文與科技之深層多元整合,以本系文學、語言學之厚實知識素養為底,再廣納本校資訊理工、管理、醫學以及其他人社領域等豐厚資源,創造多元與融合的學術環境,開拓具前瞻性及整合性之研究與學習,以培養兼具系統性思考及人本軟實力的學生,使其成為兼具在地及國際性多層次觀點與分析批判能力的未來領導者。
在研究所的規劃上,語言學方面主要是結合理論與實踐,特別重視學生在基本語言分析及獨立思考能力上的訓練。除語言各層面的結構研究外,本系也尋求在跨領域如計算機與語言的結合及語言介面上之研究 (如句法語意介面研究)能有所突破,並以台灣的語言出發,呈現出台灣語言(台灣閩南語、台灣華語、南島語)多樣性,融入社會觀察,如自閉語者聲學、聽障相關研究、社會語音學研究以及台灣語言的音變等。
相關文章

語言不只是溝通:從尼加拉瓜手語看人類心智的創造本質(台灣手語翻譯版)
你覺得語言的本質是什麼?還記得在語言學概論的第一堂課,討論這個問題時,許多人(包括我)都覺得:「語言是溝通的工具」。巨觀來看,語言確實是溝通的橋樑,但這篇文章將透過尼加拉瓜手語誕生的歷程,揭示人類發展出語言的能力或許不是為了溝通,而是為了創造更多組合。而這樣的發現,也許能引出更深一層的思考:若語言天生傾向於創造,那麼人類的本質,會不會也是?

溝通不只是「說話」:多元溝通方式的價值
許多人直覺認為「溝通一定要用說的」。然而,溝通的本質並非「能發出聲音」,而是「能讓他人理解自己想法」。語言治療領域關注的,是如何讓每個人找到屬於自己的溝通方式。作為語言治療師,我常在不同的場域看到很多人因為沒有口語,被誤以為「不會說」、「不會想」。但真正的問題或許是我們沒有用心聆聽、沒有給他們用不同的方式溝通的機會。